北京大学新诗研究院院长谢冕虽然不以研究华文文学著称,但他在世界华文诗坛,是一个闪光的名字。他的朋友遍天下,仅中国台湾地区而论,就有交往多年的诗翁余光中、洛夫、罗门、痖弦、张默和诗媪蓉子。
谢冕也是诗翁。他对这个古怪的古远清从辞典里找来的“负有诗名而年事较高者”的称谓,一定觉得怪怪的而拒不接受,因为他现在住别墅,不是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更不是柳宗元笔下出世的“孤舟蓑笠翁”。更重要的是谢冕从不觉得自己是老翁,只感到比别人年纪“大”一点而已。的确,“老”会使人想起老朽和老弱病残;而“大”,会使人联想到大有作为、大展鸿图和大器晚成。当然,这“大”也和大放厥词有关。
谢冕是何时成为诗翁的?从生理年龄上来说,大概从年过半百起,谢冕的头顶就蒙“不白之冤”。后来他的年龄越来越大,而心态却越来越年轻。作为诗歌评论领域里公认的大家,在他的所有学术专著中,诗论占有重要地位,但他的文学贡献决不止于诗歌领域,读读他的《文学的绿色革命》和《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就可看出这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为文学新潮呼风唤雨,为文学未来发展把脉和呐喊的评论家。其文学思想的变迁及其鲜活性,其文学姿态的多样性,以及谢冕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深切关怀和精确判断,人们均可从12卷的《谢冕编年文集》中看出。
在2018年秋天香山饭店召开的“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上,诗媪郑敏因行动不便未能来,孙玉石诗翁也因身体原因无法与会。有道是:惺惺惜惺惺,这次是老翁惜老翁,前排就座的全是80岁以上的老一辈诗论家:孙绍振、叶橹、晓雪、骆寒超、洪子诚、刘登翰、吴开晋、吕进……。其中已过米寿之年、来自台湾的张默堪称老大,谢冕屈居第二。
这次见到的谢冕和以往不同,他装了助听器,不像前三年在澳门大学开会时,他要竖起耳朵听大家的发言。他劝我这位坐“七”望“八”的老翁,也去买一个助听器,以便通畅地交流。在他的助听器上头,只见银发高积,可在香山与他一起漫步,他健步如飞,比谁都走得快。在大会茶叙时,我和南开大学一些诗友决定抛开学院式的话题,“研讨”起86岁的谢冕是不是美男子的问题。
通常说来,文品跟人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文章写得漂亮的人,人品也不差。但写得词采繁茂、诗意盎然文章的人,是否顔值就高呢?这次的与会者,多半是谢冕的朋友,或是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崇拜者。这些人众口一词说:“谢冕不仅文章漂亮,人也长得帅。”我不是谢冕的学生和同亊,因而我勇敢地大放厥词说:“谢冕的身材略有瑕疵。论身高,虽然不似我属三等残废,但毕竟不像张炯那样高高在上;论体态,则在‘中部崛起’……”我自认
为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评价,可我还没有说完,旁边一位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意大利学者带头抗议,说我搞的是典型的“人体攻击”也就是人身攻击,另一位日本学者也说“如果谢冕身高属三等残废,那鲁迅岂不成了四等残废了?身高与人的伟大有必然联系吗?”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说:“古远清这个人的问题不在于‘古怪’,而是满肚子坏水。他在含沙射影,且用词歹毒。”正当我说谢冕坏话引起国际公愤、苦恼着知音难觅时,来了一位写过《“知情人”说谢冕》的洪子诚,他无疑最有发言权。犹记得多年前,在南方召开的一次当代文学会议上闲聊时,洪子诚突然声泪俱下“控诉”谢冕封杀他的写诗才华。那是诗情喷发的年代,洪子诚与谢冕相识在1958年底1959年初编写新诗发展概况的时候。这时洪子诚向北大的学生刊物《红楼》投稿,可他累投累败,累败累投。而当年操稿件生杀大权的正是该刊诗歌组长谢冕。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早已模糊,他感到谢冕疑似给他写过這样一封先扬后抑的退稿信:
子诚学弟:
你将来可能是一流的学者,但你现在是三流诗人。你想做一流学者又做一流诗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
祝笔健!
谢冕拜
谢冕把学弟贬为三流诗人,难道他自己就是一流诗人?可如果说他是一流诗人,他肯定要“谢冕”,不要这顶桂冠。那他最多是二流诗人,可二流诗人和三流诗人,不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吗?一想到此,收信人也许就不会再与这位“诗兄”计较了。
弹指之间,不再做“一流诗人”梦的洪子诚,当今成了论文累投累中的一流学者,有人甚至称他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带头人。在“研讨”谢冕够不够美男子标准的“会”上,想不到他竟是我的知音。他那略带潮汕腔的口音和渗杂有 “学术性”的评价,使全场听众大跌眼镜:
谢冕是闽派评论家,闽派评论家个个都比我们这些所谓粤派评论家漂亮,如张炯、孙绍振、刘登翰无不是1米8,南帆则是美男子。
我说的闽派批评家漂亮——除谢冕之外。
真佩服这位一流学者的智慧,不似我笨拙地用写实手法描绘谢冕的身高和体态,以至落得“人体攻击”的恶名。至于谢冕为什么不漂亮,狡黠的洪子诚秘而不宣。在他看来,解释是幽默的裹脚布,正如幽默是浪漫的致命伤。
听了“知情人”这种“言不及义”的评价后,也许有人会觉得谢冕会认为这是当年的“三流诗人”在报复一流诗人。其实,谢冕的心胸决没有这么狹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和这位“学弟”也就是“北大幽默协会”的最佳搭档一唱一和:“谢某其貌不扬,世所共知,说又何妨!”
至于南开那位女教授,是谢冕的铁杆粉丝,她认为这位身材适中、“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资深帅哥老得好漂亮,因而当场宣布自己的“两个凡是”——“凡是说谢冕坏话的都是假新闻,凡是说谢冕好话的都是真新闻。”一位女博士生头一次见到自己心中的偶像童颜鹤发,彬彬如也,谦谦如也。总之是毫无老态,充满了青春活力,她竟脱口而出说:“我终于看到了活着的谢冕!”
谢冕就像是一个逆反身体衰老、有诗有会有酒有文有书有朋友便万事足的倔强老翁,
用《中国新诗总系》《中国新诗总论》等一系列记念碑式的厚实“砖”著,雄辩地向华文诗坛持续发声。每次开会,谢冕从不衣着潦草,总是西装革履。他一生爱美,对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均心向往之。他是那么爱美景、美文、美食,当然也酷爱美女。《茱蓃的孩子——余光中传》的高雄作者傅孟丽夸说自己的传主“身边的女人都爱他”,这句话对谢冕也完全适用。以这次香山会议而论,会前会后不晓得有多少美女学者争着与他单独合影留念,有的还作亲昵状。像我这位又老又古、又古又老的老古,当然没有这个福份。就连著文嫉妒谢冕“艳遇”、长得像一棵槟榔树的孙绍振,也自愧不如。
作为《庭外“审判”余秋雨》一书的作者,我有“审判”(“审视和判断”的简称)名人的嗜好。谢冕不是一般的文化名人,他早就列入我“审判”的黑名单。作为谢冕多年的诤友,我抓住这次香山论剑的难得机会,闪电式地“审判”起这位大腹便便的诗翁:
“你有高血压吗?”
“不知道。”
“你有高血糖吗?”
“不清楚。”
“你有高血脂吗?”
“无可奉告!”
我感觉到他好像在装糊涂,因而换了一个更酷的“审判”题:
“你得过老年痴呆症吗?”
这时他提高了警惕,感别问者不善,便作闭目养神状,拒绝作答。
我想他的生理现状,属个人隐私,我后悔不该“审”他,便向谢冕致歉。可他出乎意料地说:“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已被人审查过多次。你这次的所谓‘审判’,不过是小儿科。看在多年交情尤其是你编过‘略有瑕疵’的《谢冕评说三十年》的份上,我才回答你前面的‘三审’。不过,身体现状不是隐私问题,而是我真的‘无知’啊。”旁边一位博士生说:“他从来不检查身体。”谢冕接着说:“我是没有病历的离休干部,可从没有花过离休健康费的一分钱。”他在《中华读书报》上写的回忆北大往事的文章,被人误认为他在谈养生,其实,谢冕对养生之道毫无研究。他对我说:“我的健康得益于自信,没有什么养生之道。”
这位经常给中国新诗“开处方”、“写病历”的诗论家,自己居然没有病历!这无疑是个悖论。谢诗翁还自豪地跟我说自己没有住过院,开过刀,从不量血压测血糖,当然也不做B超和胸透。这位异士奇人至今仍坚持跑步和洗冷水澡。他能吃、能睡、能写、能讲、能玩。这次他作百年中国新诗的主题演讲,谈到新诗的坎坷历程时,手挥目送;谈到新诗的贡献尤其是北大的参与时,眉飞色舞。会后由企业家黄怒波也就是诗人骆英举行欢送宴会。这次宴会充分展现了美食家谢冕的“才华”,其酒量简直可用海量来形容,用他的学生高秀芹的话来说,“‘三盅全会’在他面前齐开。他的食量也大得惊人,他对美食美酒的兴趣让人感到生命的无畏和盎然。”他平时吃月饼不怕有蛋黄馅,喝咖啡一定不忘记加糖。他的一位学生请他吃自助餐时,竟一口气吃了十几只生虴。别人劝他不要吃了,可他说还没有过把瘾呢。
当然,谢冕不是某些人笔下的“仙风道骨”。他是凡人,也有小恙,这时他会到药店胡乱地买点感冒药应付。他平时不似许多老年人把药当饭吃,靠药物维持生命。远离保健品的他,现居“乡下”昌平,进城开会要换三次公共汽车然后转乘地铁,我说“坐‘八’望‘九’的老翁,不能再挤公汽了!”他反驳说:“我老吗?谁定的规矩?这规矩对我完全不适用。”
前几年在北大开《中国新诗总系》研讨会,听谢冕的高足黄子平在勺园宾馆用餐时说:“谢老师的长寿秘诀就是不检查身体。”这体现了这位诗翁的自信,当然也体现了他的文化自信。谢冕始终认为:与其相信药物,相信繁琐得令人生厌得来毫无诗意可言的检查数据,不如跟着感觉走,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所具备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使人想到谢冕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章《我的“反季节”写作》:
尽管我的季节已届深秋,我知道接着来的就是让人惊怖的冬日。人生百年,所有的人都无法躲过那最后一击。然而我依然迷恋于人间的春花秋月,依然寻找我心中的花朝月夕。
据心理医生说,影响人们心理健康的众多不良因子中,烦躁情绪与郁闷心境最具引发各种疾病尤其是癌症。而幽默风趣,不仅显出一种文化智慧,而且是一种保健良方。谢冕的幽默,不是带黄的段子,也不是刻意挖苦他人的笑谈,而是一种学问,一种气质,一种魅力。自称没有养生之道的谢冕,和他聊天,总是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记得他写过一篇散文《咖啡或者茶》。在此文中,他认为人生有两种境界:咖啡境界或茶的境界。前者是指浪漫的,后者是指现实的。在谈诗说文时,充满幽默感的谢冕,属“咖啡的境界”,可在现实中,谢冕的生活充满了暗礁和风浪,甚至还有乌云压顶的日子,人一生的一切困苦和厄运,他差不多都经历过,如在十年浩劫中,他多次被作为阶级斗争的重点对象“打入另册”。新时期到来后,他发表了支持朦胧诗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受到多次批判和“声讨”,但他没有写文章公开检讨。后来文坛上有人向他施放类似武侠片中血滴子的暗箭,还有对某位酷评家大粪浇头式的辱骂,谢冕都没有奋笔还击,而以沉默作答。另有人在天津某刋“检举”谢冕,说他在198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文艺鉴赏指导㈠》一书中,竟认为徐志摩《沙扬娜拉一首》中的 “沙扬娜拉”是一位日本女郎的名字,而不是日语中“再见”的译音。其实,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工作思想修养编辑室姓徐的责任编辑缺乏这方面知识,未经作者同意粗暴地改动原稿,致使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在家庭生活上,谢冕则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这时他突然觉得天塌地陷,奔走于毫无遮拦的暴风雨之中,他的心在流血。可他咬紧牙关,没有让这场意外的打击把自己搞垮。
谢冕告诫自己也奉劝他人将眼泪血印“放下!”除不检查身体外,这“放下”也是他展现欢容、抹去一切阴影的长寿之道。虽然普通老百姓无法做到像谢冕那样不检查身体,也不可能进入到长寿基因的研究中,但这位诗翁用“反季节写作”的勤奋著述并从中体现人生价值的实践,及其留下把肝胆俱裂的悲痛和人生的一切不愉快“放下”的忠告,却很值得我们玩味和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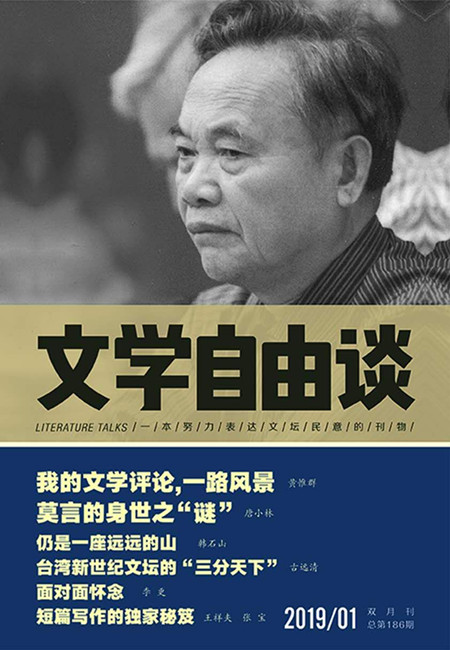
《文学自由谈》封面作者自述
古远清,粤人,与写“古怪诗”的李金发同乡,现兼职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从小家贫,父母将我卖给人贩子换饭吃,故被一位文化名人讥为“从小就没有父爱,长大了只会骂人”。和珞珈山同窗、中国社科院古继堂一样嗜好研究台湾文学,被学界戏称为“南北双古”。当这“两古”踏上宝岛时,一些分离主义者竟惊呼“两股(古)暗流来了”。我已坐“七”望“八”,成了又古又老的“老古”,但我从不觉得自己“老”,只是年龄“大”一点而已。“老”的确会使人联想到老弱病残,而“大”,则与“大器晚成”相连——当然,也与大放厥词有关。而《文学自由谈》,正是我近三十年来大放厥词的一个重要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