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韩江的脱颖而出,必然引起人们对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格外关注。近年,韩国文坛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们站在女性立场对人性的探索独特而深刻,在世界文坛已然是一股势不可挡的“韩流”。相比较中国文坛的女性主义就比较孤独了,比如在当代文坛有“文妖”之称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徐小斌,创作数十年,著作等身,却一直处于势单力薄之境。她喜欢在小说里给她的女主设置别处的世界,而她笔下变幻莫测、消弭了现实与虚幻的种种“别处”及其那“别处”里的人,却暗藏着某种执念与恪守。作为作家本人的徐小斌,似乎也与现实喧嚣的文坛保持着距离而埋首于“别处”。对于她一直处于文坛的边缘、游离于主流的说法,她的回应是:作家要面向文学,背向文坛。

一、求新求变的文体探索中不变的坚持:对女性精神困境的探究
近读2024年《当代》第四期上徐小斌的中篇《芭堤雅》,其故事的当下性、语言的爽利感全然不同于二十五年前《羽蛇》的优雅诗意的叙事风格,但作者把女主——一个天才型的影视编剧肖小冷,从现实的影视圈泥潭中拉到一个热带异域情调的芭堤雅展开故事,依然是一如既往的为主人公创设异度空间的魔法。在那样一个与日常生活不同的另类空间,奇异的发生便有了可能,比如美艳绝伦的泰国女孩的母亲被药物由美致丑,尽管这是个次要人物,却给整个故事蒙上了迷幻的巫气。小说描写的编剧女孩小冷,是个拒绝长大的女性,也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这部小说的主题即是:拒绝成长。现实中,多少人长大成人后蓦然回首,发觉自己长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人。徐小斌对此十分警觉,我觉得她是带着这份警觉塑造了《芭提雅》里的小冷。读者不难发现女主拒绝的实质并非“成长”,而是拒绝在长大过程中的堕落,和包围着长大过程的污泥浊水。 难得的是,作者并未止于对其出淤泥而不染、不甘同流合污的理想主义人格的赞美,同时写出了“如果你拒绝成长,成长就会杀死你”的警醒,更可贵的是写出了女主“我还有不死的另一半”的精神坚守,——而这正是作家在创造多变的“别处”中的不变,投射在人物身上的人格恪守。
在《羽蛇》中,徐小斌把她小说叙事的幻想性、诗意和神秘化的特质倾情灌注到女主羽身上,企图以赋予她的神性跳出凡界,来对抗格格不入的现实世界。然而羽有的只是羽毛,而非翅膀,终究逃不脱美的毁灭性宿命。和羽相比,《芭堤雅》的小冷,这个“拒绝成长”的角色,恰是徐小斌女性主义写作旅程中的一个成长的角色。
徐小斌笔下的人物总是带着某种灵异,使得她叙述的故事有一种迷幻性。比如,《羽蛇》中女儿羽、母亲若木、外祖母玄溟,这三个人物的名字皆源自神话,一出场便自带一种模糊与消弥神界与凡界的迷幻性。而徐小斌笔下所有具有迷幻色彩的人物与故事,总能在现实里找到对接,却又不那么现实,如前文提到的《芭堤雅》。这个小说的外壳是一个非常当下现实的影视圈的故事,但“拒绝成长”的内核却是抗拒现实的,与她以往的作品一样,也无法将其简单地归类于超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什么的。而且她的小说的写作风格也并不持之以恒,时常打破评论界和读者的预期,她轻易就抛开自己那些已大获成功的作品的文本风格,放弃在相对成熟的写作路径上驾轻就熟持续前行,就像一个喜欢翻行头的女子,每次出门呈现别样的面目,而这样的变换,风险系数是难免的。赫尔曼•黑塞说过,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使他驻足于世界的某一个点。用这句话来形容徐小斌小说创作的求新求变颇为贴切。
关于这一点,她在《北京文学》2024年第9期上发表的《隐秘碎片》便是近期创作最显著的例证。这部难以归入任何一种类别划分标准的小说,姑且将就给它戴上一顶“新文体小说”帽子吧。小说由四个章节四十七个断片组成,我之所以称之为“断片”而非“片段”,是因为其中的每一个都有其各自的独立性,而这独立性又有着一叶知秋的完整意义。同时,这些大大小小的“叶子”和貌似并非园丁打理的野花,则构成了一片仿佛野蛮生长的原野。评论家贺绍俊教授称《隐秘碎片》的构思和意象是“灵感出窍”的非理性产物,我则更愿意视其为诗人的诗性思维的呈现。我从第一次接触徐小斌的小说,就固执地认为她的小说是诗性的叙事,她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寓言性隐喻,是具有哲学探索和诗的气质的不分行表述。回到徐小斌创作的女性主义母题上,这部《隐秘碎片》的前两章,几乎每一个故事都以女性为主人公,其名字则是这些故事序号的谐音,颇有意趣。后面两章虽有“他”做主人公,却仍是女性视角的他或他的心理。整体读来,这部小说的“性特征”非常强烈,所谓“隐秘碎片”,在我看来是作者站在女性立场的各个视角的伸展和女性心理的万花筒呈现。所以,无论徐小斌在文体上如何尝试新的花样,呈现新的变体,有一点不变的是,从她的成名作《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至今,她的七百多万字的作品,都专注于书写女性,孜孜不倦地深入女性的心理版图,探究她们在现实生活和文化语境里的困境,而这困境又往往不是衣食住行那样肉眼可见的物质层面的,而是在失去灵魂的世界里,人的灵魂的困境。

二、寓言性写作:与卡尔维诺和罗伯•格里耶契合中的不同
当然,徐小斌并没有能力将女性,包括她自己从此处的现实困境中解脱出来的,于是,她用文字构筑一个个“别处”。她创造的一个个“别处”,其实是她为成年人书写的寓言,那些在现实里遭遇不公对待,而不被看见、不被说出的人,徐小斌让她们在“别处”被看见、被说出,那些在现实里逆行的人,在她笔下的“别处”获得共情。说到徐小斌小说的寓言性,我就想起以奇特想象创造寓言小说的卡尔维诺。
今年春节前夕,徐小斌发给我一个小视频,是为“好书探”推介她这年里读过的一本好书:《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记》,她称卡尔维诺是自己始终热爱的一位作家。想起两年前,她为我主持的公众号《Meet域外典藏》做“经典荐读”,当时她在卡尔维诺和罗伯•格里耶之间犹豫踌躇,最后推荐了后者的一个中篇《吉娜》。也许是卡尔维诺太丰富了,反而难以选择。莫言曾说:“ 有一段时间我似乎是理解了,后来一想什么也没理解,因为他的头脑实在太复杂了。” 看到小斌在“好书探”视频里娓娓道来她热爱的卡尔维诺,我不由会心地笑了。
一个作家喜欢的另一个作家,一定与其本人有某种气息相投。相信徐小斌不管推介谁,都会是选择那种超越传统、独辟蹊径的另类,并在文字里构筑一个非现实的奇幻的“别处”。以她本人十六岁就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经历,一定有许多值得痛说的苦难,但她并未去写《今夜有暴风雪》那样的知青文学,而是跳脱开自我,与亲历现实拉开距离,进入人物神秘的精神之域。然而,她在她创造的神异空间里,从未离开对现实中女性命运和人性深层隐秘的探索。每每走进她的小说世界,我都有点眩晕迷离似真似幻的感觉,每次放下她的小说,我得使劲晃晃脑袋,让自己定定神儿。难怪她在中国文坛有“文妖”、“巫女”、“落入凡间的精灵”之称。
有件事,很是不可思议。
八十年代末,在上海街头一个拐角看到一张《孤光》的电影海报,我一直记得那海报上还有一行字: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许多年后,温哥华一间咖啡馆的徐小斌读者见面会上,隔着一张小小的咖啡桌,近距离地看着她,听她讲述自己的创作和在黑龙江令人难以置信的知青生活,脑海里竟莫名其妙地浮现出那张电影海报,但“弧光”两个字模糊了,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清晰地横在我眼前。事后上网搜那张海报,令我吃惊的是,那上面根本就没有“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这行字!
这是徐小斌一部中篇小说的名字,由第五代领军人物张军钊搬上银幕,编剧是徐小斌本人,并获得1988年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不过老实讲,我当时看到那张电影海报时,真没注意谁是编剧。可奇怪的是,我的记忆里执着地把原著名字放在电影海报上。至今我都没想明白,是不是徐小斌小说的那种迷幻的巫气所致,还是我自己就有点她小说里的人物时常出现的魔怔?
这件事令我对徐小斌当初为何向我推荐罗伯•格里耶,以及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有了某种顿悟。徐小斌说她自己在最初接触到这位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的作品时,就被作家在小说里轻而易举就抹掉了过去、现在、未来、现实和梦幻、生与死的界限而震撼了。在2005年罗伯•格里耶第三次访华时,徐小斌有幸见到他,并与之对话,而那时徐小斌已经出版了她的长篇代表作《羽蛇》。对于本就深陷于幻想世界的徐小斌,最初读到罗伯•格里耶小说,犹如是暗夜里的一道闪电,而见到其本尊并与之对话,令她更为自信和执着地与文坛的当下保持距离,醉心于构筑她自己的“迷幻花园”的实验:把最虚幻的形而上空间与最现实的生活结合起来。她的小说的寓言性,和卡尔维诺所不同的是,她会在寓言的内核外包裹一个现实层面的活色生香的故事外壳,在新作《杀死时间》和《芭堤雅》两个中篇里,呈现得尤为突出,因而也增强了她的小说的可读性和可视性。但她绝不会止步于表层故事,所以她也不会放弃她的建构“别处”营造迷幻的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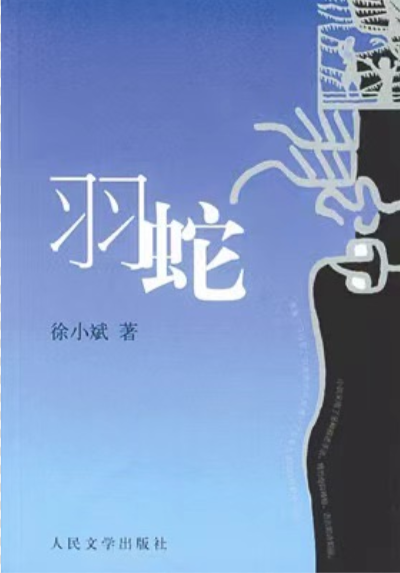
三、“神镜”的穿越与女性主义人物的未知空间
在她的许多小说里,都可以看到她的叙事穿越了时间与空间、虚构与现实、上帝与魔鬼、此岸与彼岸的界限,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转换。如此,她就跳出了外部叙事的局囿,而进入内部叙事的幽深诡异,并在内外进进出出,抵达广阔的富有张力的自由叙事的境界。仿佛是掌握了一面中国古代神话里的神镜,入镜就到达了彼岸;出镜就回到此岸。当我跟她要一篇她自己的作品作为公号里“当代原创”的推文,她发来了《银盾》。在这个短篇里,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道具的银盾,就有点神镜的意味。但徐小斌绝非在进行传统意义上的神话传奇的叙事演绎,她只不过是借助神话的超现实性来更便利地揭示现实中的残酷,这种方式本身其实是在解构神话,从而创造出一个打破神界与俗界藩篱的、充满“智性与诗情”的异度空间。而在神界与俗界之间,蕴含着作家有关女性、欲望、焦虑、边缘等种种潜意识问题的探究。
《银盾》讲述了一个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的乡村女孩儿蜂儿,在追寻母亲死亡真相过程中的离奇幻境,而她经验的幻境与现实不断纠缠、扑朔迷离而又互为印证。作家让那个躲在银盾背后的脸始终没有正面暴露,这个设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寓言,也是银盾所隐藏的谜底。这让我想起19世纪那些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诸多虚伪的却总是在台面上风光的可憎面孔,比如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的两个旧情人和那个虚伪又歹毒、最终却戴上了骑士勋章的药剂师等卑劣的人物。与批判现实主义经典大师犀利的正面刻划所不同的是,徐小斌试图创造一个复杂、多义、混沌、抹去虚幻与现实相接痕迹的空间,提供给读者在多方位空间里体验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比如,她让读者可以拼图出来那个藏在银盾后的可憎面目,但在小说勾画的现实空间里,背叛者终究未被揭露,仍冠冕堂皇地主持着戏班子,该上演什么照旧上演。在此,又一次呈现了贯穿在徐小斌小说世界里的女性主义的一种深刻的潜意识形态,正如戴锦华在《自我缠绕的迷幻花园——阅读徐小斌》一文中所指出的徐小斌小说揭示了:“女性对男性的复仇永远只能在想象中完成,而男性对女性的侵害、叛卖却要真实得多”。
然而,不甘于驻足于原点的徐小斌时常会让评论家措手不及,比如获得2023年人民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杀死时间》,似乎是对戴锦华上述论断的一个颠覆。徐小斌在这个小说里扮演了一个邮差“我”,貌似以男性为主角的故事,而围绕在他身边的配角皆为女性,她们原本处于被男权抛弃的劣势地位,而故事的结局,她们全都令人惊诧地反转成为独立、自由的女性,男权在她们那里轰然坍塌,作为读者的我们跟着小说男主“我”,一道面对着彻底打破预期的结局而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小说在直面现实世界的人情冷暖、书写出以邮差为代表的当下底层青年在生活的艰难中不失善良本性的同时,抛开了社会道德层面的约定俗成,非常狠辣地写出当代女性不再依赖男性的独立决绝,甚至包括生育的独立自主权和能力。与传统女性为了金钱而委身依赖男性迥异的是,这个小说里的海归女和IT女都是凭借自身的能力,撑起了自己头顶的一片天空。不过,徐小斌无意把她们塑造为世俗的“励志”形象,却不惜让她们背负现世社会道德人伦的非仁义,而完成她们自身独立的人格。
女性主义人物的命运,在徐小斌的笔下仍有许多未知的空间。

四、现实主义的书写无以抵达,而在“别处”蕴含巨大的野心
从上世纪成名作《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刻画的“精神病”女孩儿景焕,到后来《海火》《羽蛇》《水晶婚》《双鱼星座》《 迷幻花园》《敦煌遗梦》等作品中一系列女性形象,徐小斌似乎一直在努力着一件事,她与世俗现实保持距离,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其敏锐的感受力结合超拔的想象力、在广博的知识储备之上挥洒异禀的智性、融神性与诗性于一体,在小说世界里构筑起一个个诡谲神幻的“别处”,而这些别处,绝非只是追求奇异的别出心裁,而是蕴含了作家巨大的野心:她在解构父权专制下的母系社会的同时,企图建构新的女性社会主体价值。而这个企图在现实主义的书写中几乎无以抵达,她只能在“别处”追寻。
徐小斌曾这样说:“归根到底人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屈从于外部的强力与诱惑,放弃自由出卖灵魂,换得世俗意义的幸福,而另一种是对抗,是绝不放弃,这样可能牺牲太大,但是这样的生命或爱情可以爆发出瞬间的辉煌,这样的生命注定短暂,但却真实,它的质地与密度无予伦比,这样的人可以说他真正活过了。” 这段话中,可谓是徐小斌对于始终暗藏于“别处”的那份恪守不经意的一次说明,从中不难看出她是个内心具有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作家,她的“别处”就是实现其浪漫主义的所在,一种玄奥的形而上的空间。她在此处与别处的二元对立中,使其笔下的世界极具现实与梦想的张力。而那空间里的女主们,正是如作家所说的另一种活法的化身。
想到卡尔维诺曾说:“ 我始终渴望着别处” 。卡神的别处,并非只是地理空间的另一地方,在《树上的男爵》里,作家让他的主人公在树上摆脱地面的困扰。而徐小斌的“别处”则是将此处现实里被困的、遭受种种不公的女性,到自己笔下的“别处”还她们公正。但需要指出的是,徐小斌并非是把“还她们公正” 局限于两性之间,或者说只是从男性、男权那里讨公正,她的女性世界不是二元对立的女权主义,她笔下的女性之间的争斗,一点也不比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斗争更轻逸,比如《羽蛇》中的母女关系。在父权夫权社会中的女性,在某种条件和位置上,她们的角色就从女性变成了女性外貌的父权执行者。徐小斌的女性主义书写跳脱了女性与男性表层的社会争斗,而是返回女性自身,把女性置于她们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社会、整个宇宙世界,也面对女性自身。比如《芭提雅》中的女主编剧肖小冷,与时不时挂名“总编剧”“总制片”的大导演老婆夏月之间的博弈。夏月这个人物在小说里虽着墨不多,却是颇具深意的人设。虽然同为女性,小冷是纯粹的女性,拒绝被污染的女性,而夏月则是背靠男权的异化女性。作为女性,她其实已经失去了女性本质的内在力量,但却是现实中的强势女人。
从《羽蛇》到《芭提雅》等多部近作,徐小斌执着地书写着现实中被边缘化却坚守女性内在人格力量的她们,而她确也在创作中如她自己所言“尽力去寻找一种边缘情境:弃绝一切外部装饰之后的原初与归属、可以表达哲理与诗意的寓言式写作。“离开了翅膀的羽毛的命运,徐小斌已书写得淋漓尽致,而翅膀上是否新羽再生?在她的近作中,我看到了不止一种新生。

(部分节选首发《文艺报》2024年12月13日“文学评论”版; 全文以《徐小斌的女性主义别处》为题,刊载于2025年第2期《新文学评论》)
